東西問丨吳飛:中國大一統格局緣何與禮樂傳承息息相關?
中新社北京7月22日電 題:中國大一統格局緣何與禮樂傳承息息相關?
——專訪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每個時代、每個場合中,每個人如何恰當行禮皆有一定之規,巨細靡遺的禮制體現著中華傳統禮樂文明的動態之美。
“我們今天對禮樂之美的繼承并不是對具體禮制的繼承,而是對禮樂精神的繼承。”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在《禮樂傳統中的大一統》一文中提出,禮所體現的是文明、善意以及和平,這正是“大一統”理念的核心所在。
為何中華文明傳統以禮作為大一統的標準?中國大一統格局的形成,緣何與禮樂精神的傳承息息相關?在研究禮樂傳統與大一統關系時,如何避免狹隘民族主義?吳飛教授就相關話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何中華文明傳統以禮作為大一統的標準?
吳飛:中華文明傳統以禮作為大一統的標準,是一個相當有彈性的區分標準。所謂“禮以義起”“禮,時為大”,禮是以尊重自然、尊重歷史為前提的一套秩序,其具體規定隨時代不同而改變和調整。
以夷夏之辨為例。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意指只要符合禮樂文明的標準,不論民族與宗教信仰,都被視為中國的文明人,否則即便血緣上是中國人,但行事非禮,則視為夷狄。
這一原則在中國歷代王朝中都有體現。以唐朝為例,唐朝皇室有鮮卑族血統,其所開創的大唐盛世,向來被視為中華文明歷史上的頂峰之一。遼、金、元、清等不僅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還往往具有宗教信仰的復雜性,但都融入了中國大一統體系。對于大一統的體系而言,民族、宗教都不是問題。
這種大一統,不能理解為簡單的漢化。無論是元朝的蒙古族,還是清朝的滿族,在接受傳統禮樂制度的同時,也有意保留了民族特色,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作出貢獻。
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西夏陵真實、完整地保存至今,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見證,也是多民族共同締造中華禮樂文明的實例。

中新社記者:從禮樂傳統的時空內涵看,每朝更替先制定本朝禮樂制度的傳統,從哪些方面體現了每朝每代統治的“大一統”格局?
吳飛:古代禮制分為吉、賓、嘉、軍、兇五禮。吉禮中,首要的是祭天禮,它是天人關系的落實,是一個王朝合法性的體現。因此,每朝更替之時,都要制訂自己的歷法,以及相應的郊天禮模式。《春秋公羊傳》中“大一統”一詞的本義,指的是“張大最重要的歷法”。
具體來說,一方面是“通三統”,即尊重前朝歷史,另一方面是前朝歷史不能干擾現實秩序,即“大一統”。比如夏、商朝、周三代有各自歷法,周尊重夏、商的歷法,與自身歷法“通”為“三統”,但王朝內不能并行三種歷法,而要以周的歷法為唯一官方歷法,這就是“大一統”。
可見,大一統是為自己確定一個歷史定位,郊天禮也正是這種定位的結果。按照漢代經師的解釋,周是木德,所以郊天要祭祀東方青帝,同時有以春季為重的歷法,因為東方青色對應于春;秦自認為是水德,對應于冬,因此以十月為歲首;漢是火德,郊天要祭祀南方赤帝,同時有以夏季為重的歷法,因為南方赤色對應于夏。以后的朝代慢慢不再完全接受這些具體的理解,但都有自己的時空定位,并通過歷法、郊天禮和本朝的一些特色制度展現。隋、唐、明、清等朝代舉行郊天禮的天壇,都有助于今人理解禮樂文明體系的演變。

中新社記者:中國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在哪些方面與禮樂精神的傳承相關?
吳飛:禮樂傳統是非常有彈性的,特別反對教條化。可以通過樂來反觀禮。以中西音樂為例,西方音樂,一位作曲家創作出一首曲子,此曲則為其作品,后人見其曲譜,便可拿來演奏,但此曲不屬于演奏者之作品,若演奏與譜子不同就是錯了。中國音樂不是這樣的,古人的工尺譜并不能演奏,因為它只是對一首曲子走向的大致描述,后人必須根據自己的理解打譜,才能把曲子演奏出來。這個曲子很難說是最初寫譜的那個人的作品,后面每個演奏者要再創作。
禮也如此,今天的人讀“三禮”,可能會覺得非常繁復,這是因為時代太遙遠,讀起來有障礙,不容易理解。《儀禮》中規定的一種禮,比如《士昏禮》,共3000字左右。有現代學者試圖按照《儀禮》中的流程把這些禮表演下來,結果發現其中很多細節是根本沒有規定的,所規定的只是一些必要的環節和原則。《禮記·大傳》中說:“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那些具體的細節,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可變的只是一些原則。我們今天繼承禮樂文明,就應該了解這些原則,即禮樂文明的基本精神。正是靠著這些原則,中國才會形成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格局。

中新社記者:在談到反對禮學研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時,您曾說,“甚至有些更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對清代的成就一概否定,儼然一副反清復明的姿態,以為凡是清代的禮儀都不可用。”在研究禮樂傳統與大一統的關系時,如何避免類似的狹隘民族主義?
吳飛:狹隘民族主義是今天談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時特別容易陷入的一種偏見,也違背禮樂文明基本精神。禮樂文明,是文明傳承中用來理解自然、歷史、政治、社會的一種方式,不能把它理解成僅僅一種民族特色或標記。各民族對于中國大一統的禮樂文明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周禮》中的政治制度落實為六部制度,是在鮮卑族政權北周實現的;今天仍沿用的行省制度,是在元朝建立的;今天中國的民族和疆域格局,則是在清朝形成的。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禮制。正因有了禮樂傳統,中華文明才通達知變,不固執,不教條,存在發展的可能性和創造力,這是我們寶貴的遺產。如果以狹隘民族主義的方式面對這些遺產,就與禮樂文明背道而馳了。(完)
受訪者簡介:

吳飛,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比較哲學、禮學、經學、基督教哲學、宗教人類學。著有《麥芒上的圣言》《浮生取義》《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人倫的“解體”》《禮以義起》《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解讀》等。譯有《上帝之城:駁異教徒》《蘇格拉底的申辯》等。

東西問精選:
- 2025年07月22日 16:28:47
- 2025年07月22日 14:59:21
- 2025年07月21日 17:48:19
- 2025年07月21日 17:34:28
- 2025年07月20日 14:41:54
- 2025年07月19日 17:07:57
- 2025年07月19日 14:29:32
- 2025年07月19日 13:00:45
- 2025年07月18日 21:52:39
- 2025年07月18日 18: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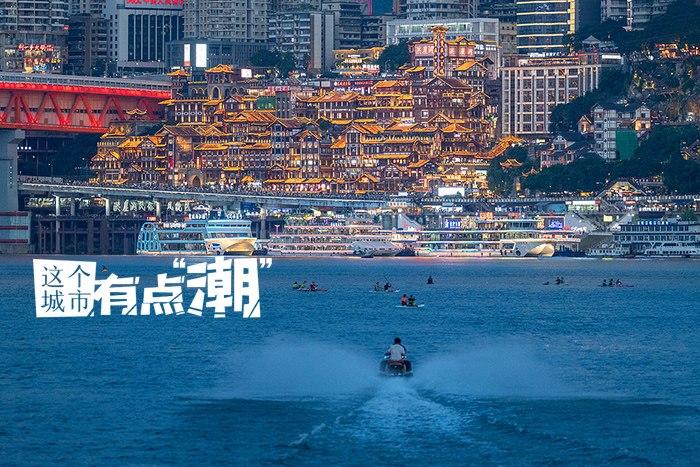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